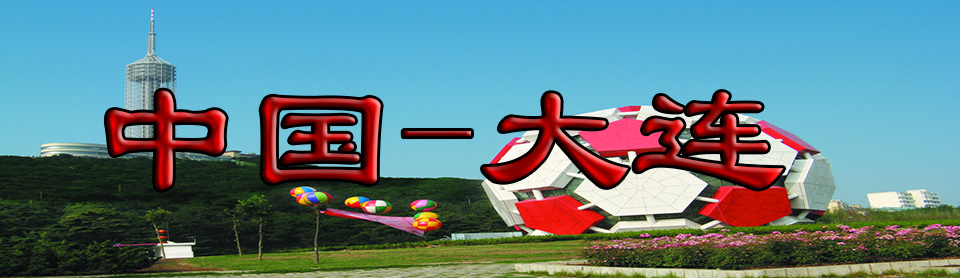传承丨素素讲历史大连的流光碎影八
驿站
走进牧城驿,完全是一个偶然。那天,我本来是去营城子看汉墓,从汉墓出来,路过一片果园。这个果园的主人是一位老朋友,他会作曲弹琴,还喜欢读书,做别的生意挣足了钱之后,在这里种樱桃苹果葡萄之类。他其实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。所以,我从来不叫名字,就叫他庄园主。
在果园饱吃了一顿大樱桃,见天色已近黄昏,庄园主就开车送我回市内。车子路过牧城驿,庄园主又突发奇想,说,我再带你去看个城吧。我问,什么城?庄园主说,明代的城。我问,哪里有明代的城?庄园主说,牧城驿就是呀!这一带就剩牧城驿没去过,原来它还是一座明代的城。见我来了兴致,庄园主马上就开车拐了进去。
这条古老的驿路上,不仅有牧城驿,还有孛兰铺,即普兰店旧址
这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街,不直,也不宽阔。两边的房屋有新有旧,排列得很零乱。因为是傍晚,卖菜卖衣服卖书报的小商小贩已经把货摊挤到路中间了,吆喝声此起彼伏,确有一点古城气氛。车子没走出多远,庄园主就向外指了指说,这是北城门。我拧疼了脖子,也没看见北城门在哪里。车子向前又走了一会儿,庄园主指了指说,南城门到了。我左右看看,还是没看见城门在何处。这时候,庄园主叫我下车。
虽然还是在这条狭窄的南北大街上,南城门却比北城门清静多了。只有一两个小商贩蹲在自家门口,不吆喝,也不拉扯,目光闲闲地望着我们。街东侧有一堵石砌的旧墙,庄园主用手拍了拍说,这就是南城门。果然是城门,墙角有块今人用水泥抹出的碑,上面刻了两个大字:明城。字也是今人所写。然而,我还是惊奇地凑了过去,对那一堵旧墙打量起来。它是紧挨着南城门的一段城墙,如今它成了街边一户人家的院墙。墙上面还有几层青砖,那青砖显然是昔日的城门拱。我连招呼也没打,就钻进那户人家的院子里,想看城墙究竟有多长。那家的老人说,嗨,姑娘,就剩这一块儿了,我天天看着呢。
于是,我拉着庄园主从南城门走回北城门,想从头至尾地看看这座城。与南城门一样,北城门也只有一堵旧城墙,而且也在街的东侧。在小商小贩们的叫喊声里,我走进了靠城墙边的那家卖书人的小屋。我以为可以从他家的后门看到什么,可这间小屋根本就没有后门,只好再回到古城的街上。
庄园主知道我这一阵子正在找城,而且知道我没去过牧城驿,所以,在就要与它擦肩而过的时候,决定把我带到这里。对于我,这是意外的收获。
牧城驿南城门
明朝初年,因辽东沿海屡有倭祸,明廷决定在辽东一线设置卫所。辽东半半岛由南向北,分别有金、复、海、盖四个卫所。在卫所境内,曾设有许多烽火台,以此传递军情消息。除了烽火台,还设了许多快马驿站。金州卫境内,就有石河驿、金州驿、木场驿、旅顺驿。木场驿是明代的名字,清末改叫牧城驿。因为过去这里曾是一片茂密的森林,而且有一个伐木场,所以就叫木场堡。在当年,堡就是驿。从金州卫出发的堡,向北有二十里堡、三十里堡、四十里堡、五十里堡,这是由陆路往复州卫飞报;向西南有革镇堡、木场堡、三涧堡,最后一个堡,当然就是旅顺口了。在明清两朝,不论是以前的堡或是后来的驿,它们都是为战争而设的另一种形态的工事,只要狼烟一起,就会有快马在堡或驿之间奔驰。我以为,在那些驿站上,可能只有一根拴马桩,早已不知被历史的长风吹到哪里去了。想不到,牧城驿不是一根木桩,它在明代就是一座石城。
那个正坐在街边乘凉的男人似乎明白我要看什么,他指给我一个梯子,让我爬上他家的房顶,鸟瞰整个牧城驿。我发现,城内没有一座高楼,那些新盖的房屋,大都没超出旧有的建筑。古城南北狭长,被夹在了东西两座小山之间,蔚蓝色的渤海湾涌动在它的背后。我就想,在它作为驿站的那些日子里,那来来回回的信使一定传递过什么样的好消息或坏消息,这里一定发生过不同于别处的故事。可在我以往读过的书里,居然没有一页是对于它的描述。那一匹匹匆匆奔跑着的马,那一队队匆匆奔跑着的将军和士兵,从这条驿路上消失之后,便只剩下了这座古城。就像营城子地下的那些古墓,只可以用“炭14”推断出年代,却无法知道主人是谁。
庄园主的老家就在牧城驿。见我站在房顶上,他也爬了上来。庄园主说,在他童年的记忆里,这个城与别的城不一样,它是一个狭长的不规则的船形城,南、北、东三面城墙都是石砌,西城墙却是土夯。听老人说,古城也并不是明代始建,而是唐初高句丽将军盖苏文占据辽东时所修,明代在唐代古城的遗址上筑城设驿。这只是一个传说。据史书记载,明朝末年,辽东总兵毛文龙确曾派兵在这里驻守,而且把土城改为石城,因为是最后一次修缮城垣,后人就说它是明城。
我明白了什么叫荒凉。一座古城明明有更深远的历史,却没留下记录那历史的文字,这就叫荒凉。荒凉的杀手当然是战争。辽南的荒凉,乃至整个东北的荒凉,全都是因为战争。一场战争,一层焦土,一片空白。绵长的历史,就这样被切割成了互不相连的断片。
从这一作明代的城墙可以看出,牧城驿还属于一个简陋的战争工事
那个傍晚,我们没有再坐车,而是步行走出北城门。庄园主似乎看出了我的失望。他说,找个时间再来吧,牧城驿其实是个大屯子。
大屯子。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称呼,明明是城,却叫大屯子。许多天后,我果然再一次好奇地走进了牧城驿。
它原来是在明与清最后那一场激战里被遗弃了,空落了,荒芜了。数年后,康熙皇帝诏令辽东招垦,才有一批批移民者拨开荒草,试探着走进死寂的城内,城也才从一场噩梦里苏醒过来。自此以后,牧城驿就不再是一座驿站,一座城,而是一个村落。三百年历史的村落,的确是大屯子。
庄园主引我来到古城西街一座农家小院。主人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者,高高的个子,乐观而且健谈。我们就坐在他家种着辣椒西红柿的院子里,听他讲大屯子的故事。
老人说,最早来牧城驿的人叫占山户,因为靠海边的平地是一片芦苇荡,开垦起来太费劲,在山上开荒种地可以当年就吃上粮食,所以所有的山地都叫先来的人占去了。后来的人也要种地吃饭,没有山地可占,就只好去占海边的平地。他们在芦苇荡里开荒虽然非常艰苦,可真正的富户就是这些占平地的人家。后来者居上。这大概就是大屯子历史开篇时的悲喜剧,也是大屯子备忘录里的一个章节。
也许是屯子太大了,以古城北门外那条路为界,分了两个牧城驿,住在城里的叫前牧城驿,住在城外海边的叫后牧城驿。在外人眼里,前后都是一个牧城驿。牧城驿有二十个姓。给我讲故事的老人姓董。他把这二十个姓编成了一个歌谣,当场就亮起嗓子唱给我们听:王张董韩刘,程毕崔杨由,李于郭辛谢,苏胡仲黄仇。唱完了之后,不放心似的要过我手里的本子,仔细地检查了一遍,生怕我把哪一个姓写错了。
大屯子必有大姓,大姓必是大家族。姓和家族代表着一种尊严。在牧城驿尤其如此。董姓老人告诉我,牧城驿的每一个姓,每一个家族,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,在各自的祖宗家谱上,都写着一串传世字。日子过得体面的人家,还有堂号。堂号是户主给自己家门命的名,与外界往来,彼此之间叫堂号比直接叫名字要显得雅重。比如三多堂、心一堂、福顺堂、久大堂等等,牧城驿当年有十几家堂号。有堂号的家,有砖有瓦。如果说谁家有砖有瓦,就等于说谁家日子过得富。
牧城驿最显赫的是李姓,据说李姓门下曾出过一个翰林,于是在李家的院子里,就竖起了一只高大的旗杆。给谁竖旗杆得皇帝说话,不是谁想竖就可以竖的。直到现在,牧城驿人还管李姓叫“旗杆底李家”。在大姓里面,人口最多的是韩姓,韩姓又分大姓韩和小姓韩。分出大小,有的说是为了跟官府多要粮饷,也有的说是怕遇着祸患株连九族。后一种说法更贴谱儿,因为牧城驿做官最多的是韩姓,最大的官做到侍郎,官阶四品,最小的官是校骑尉,官品虽不高,也是祖宗的荣耀。老人小的时候,总听家人嘴里念叨什么尉老爷、皋老爷、萃老爷。可见韩姓一门出了不少人物。韩姓子弟在当今也做得很成功,有在北京做副部级大官的,还有在海外做大商人的,这说明韩姓祖上有德啊。据董姓老人说,韩姓家族的祖先,可以上溯到明末,每一支每一辈,走过哪些地方,什么时候迁来的,历代祖先的名字,都写在族谱上。大韩小韩都有族谱,修族谱一直是韩姓家族的传统,最早的族谱是明末清初修的,还有序,那文言文写的叫好。
这就是大屯子人,把族姓看得很重,把荣誉看得更重。原以为一姓不说另一姓,董姓老者在说李姓和韩姓的时候,却像说自己家一样高兴。大屯子之所以能成大屯子,大屯子人不但有尊严,还有胸怀。
记得,那是长达一个下午的谈话。我没想到,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有这么强的记忆力,各家各户,大事小情,都能说得头头是道。牧城驿谁家开过商号,第一个自行车铺的老板叫什么名字,山上碑楼里竖了多少块贞节碑,古城内外有几座庙,大户人家的婚丧嫁娶如何排场,等等,全都装在他的脑子里,说的时候,掩饰不住就有一种自豪流露出来。在辽南乡下,我从未见过哪里有这样古朴这样规矩的大屯子,我不知道有哪个屯子能经得起这么长时间的说。给我的感觉,它是纷繁的,又是秩序的,是复杂的,又是纯洁的。男人对功名的渴望,女人对贞节的坚守,子孙对诗书的沉迷,使它更像文化淳厚的中原古坊。庭院深深,古香古色。我真希望能在这里住下来,能一个姓氏一个姓氏的倾听。因为它太珍贵了,我真害怕它有一天会改变得面目全非。
也就是那天,当我再次徜徉于古城大街,突然在北城门书摊上发现了一本写牧城驿的书。书的名字叫《辽东古邑——大连牧城驿》,作者姓韩,牧城驿人。他在书中说,因为读大学离开了牧城驿,在外做了几十年游子后回到故乡,并在七十岁前出版了这本书。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它,它实际上是一本村志。在这本村志里,我看见了牧城驿古城的几张老照片,它们是一个韩姓子弟出国留学前所拍,时间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。那时候,南北两个古城门完整而且威严,古城中心的小广场上有两座庙,一座关帝庙,一座娘娘庙,庙前还有两棵参天的古槐。那个韩姓子弟依恋地站在它们前面,一处一处地留影纪念。
这就是历史,在它离去的时候不会走得干干净净,总要遗落一些什么,等待后来的人去触摸。
村志上说,古城和古庙是在文革中被拆除的,古槐也是在文革中被砍倒的。看来,古城的消失,只是近几十年间的事。好在还有一块碑在,有两段残墙在,有牧城驿这个名字在。
长按识别白癜风的初期症状表现什么治白癜风
转载请注明:http://www.dalianshizx.com/dljt/6806.html